前兩天發行《丙申年》猴票時,莊里郵迷在欣喜之余,更多的是不滿。一是因為一大早就來排隊,卻只能買到一枚,而往年則是每人能買一個四方連。另一件事就是,在排隊買猴票時,長安郵局發生了有史以來未有過的兩件事:先是因為排隊者發生了爭斗,叫來了110;之后便是一位年逾八十的老者,在排隊中暈倒在地,又叫來了120,幸好到醫院搶救后,醒過來且無大礙。
這兩件事我都沒親見,因我是在河北賓館參加首發式,本以為參加首發式也能買到猴票,但那里根本就不賣。有人說,《丙申年》郵票印量達3億,這不一定是準確數字,但估計也不會比去年的少。因此,造成這樣的“緊張”,純屬人為因素。郵票販子手中,就有大量貨源,從何而來?根源還是在郵政。因此,郵政部門是難推責任的。據說,上海首發售郵票時,老年會員是不用排隊的,可以到專門地點取票。但可惜,上海這種人性化的做法,并沒有得到其他地方的郵政部門效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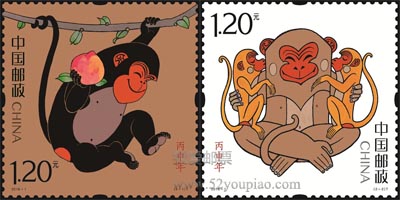
記得很多年前,一位新加坡郵友,商量和我約定互寄首日封,我當時便謝絕了他。但這位海外的集郵者還是追問我為什么?我說,我當天不能買到富余的郵票,他表示很驚訝,怎么會這樣?我說,我們是預訂的,不能多買,他表示不能理解。的確,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和地區,郵票都是不憑預訂證的,在新郵發行的首日,也不限量購買。唯獨我們,中國特色。這個“特色”,產生了很多弊病。記得當年《庚申年》猴一世發行時,根本就沒有什么預訂證,郵局也不限量,你可以隨便買。正因為如此,才有大量“猴”票被“信銷”了;也正因為如此,在今天,才有人可以制作《庚申年》郵票的郵集,來向大家展示郵票的印刷差異,以及大量的各種樣式的實寄郵品。否則,他就不可能做到。可見,這個預訂制度,無形中“扼殺”了多少郵集啊!
關于預訂制度,本來目的是為了解決供求關系的矛盾,現在看起來這個問題并未解決。反倒引出了“惜售”和“破版”、撕掉邊紙等損害集郵的現象。早就有郵友批評過,“改革開放,所有的都由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,唯獨郵票發行還是計劃經濟”。如今,“首日難買到,日后賣不掉”的現象已經是司空見慣、習以為常了。
當今的郵票,已經失去了使用價值,而只有收藏價值。唯一要使用的人群,就是集郵者中的“原地”、“首日”和“極限”郵品收集者。但這些人,都被“預訂”制度所束縛而不能隨心所欲,久之,自然是積極性受到打擊。不能隨意買票,買票要耗費時間和精力(據說為了買猴票,有人三點便來排隊),當集郵成為一種折磨和痛苦,自然就會使一些人遠離而去。
今年的猴票,我到現在一張沒有,當天只給一些朋友寄出了戳片。外地郵友也大多是寄的戳片,首日郵品很少。一位和我交往了幾十年的摯友,寄給我的一個“猴戳郵品”,讓我欣喜之余更多的是傷感,同時也理解這位郵友和我一樣的無奈,以及無奈之余的煞費苦心。
這位郵友由于買不到猴票,居然貼上了1991年發行的J180《第十三屆國際第四紀研究聯合會大會》郵票,其原因大概是因為這張有票有“中國猿人”的圖案,總算是找到了一個“接近于猴”的圖案。至于“類人猿”和“猿人”的區別,那就無法深究了。
這枚實寄郵品,幽默的表達了集郵者的“無奈”,也引出了我這一番廢話。集郵,真的很累了!什么時候,郵票的發行,能夠效法一下近期銀行的“流通紀念幣”的發行辦法,那就好了。但我說好是不行的,恐怕有的人會斷了財路的。作者:博事候
 粵公網安備 44030602002232號 |
粵公網安備 44030602002232號 |